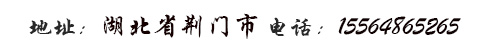三清山上话杜鹃
|
清明过后,我前往三清山,行前询问上饶的朋友,其略带婉惜道:只怕是杜鹃谷的花儿还没开呢? 她这样一讲,倒真让我有些念想呢。小时候看样板戏,唱电影歌曲,“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江西革命老区的映山红便是杜鹃花了。 还有一部电影《杜鹃山》,也是以杜鹃开遍山野的场景来彰显游击革命斗争的。记忆犹新的台词就是“大哥,咱们下山吧!”,其目的就是让革命火种离开火红的杜鹃山,下山即中反动派军队的圈套,可是叛徒温其久骗不过“女旗手”柯湘的火眼金睛。柯湘依靠杜鹃山上的革命群众,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红色文化教育出来的孩子,使我从小明白,杜鹃花是英雄的花,革命的花,理所当然,也是红色的花,再说了,花的别名就是映山红。所以在我的认知里,杜鹃花是红色的。好比地球人认为天鹅一定是白色的,直到人们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才纠偏。 八号下午,我从外双溪索道上了三清山,坐着缆车如坠入云雾中,窗外只有几根钢索可见。山上雨雾天气,我只好拍些近景花草什么的。毕竟,阳历已是四月,山上可觅得阳春的气息。 在南索道站前往日上山庄的路上,我看到白色的树花,洁白无暇、不像真花、朵儿较大、仙山奇葩。雨雾天气,花瓣上带着晶莹的水滴,鲜花沐浴后似美胴出浴,这白花儿鲜亮明丽、洁净精微、清澈无暇,在雾蒙蒙的阴天煞是醒目醉人。 一见此花,便生爱怜;再看此花,更生诗情。 繁花逢雨水, 濡首赏花人, 三清雾所有, 聊摄几枝春。 只是这无名白花让我有些失落,就象见到美丽的女子,却不知她的芳名,有些怅然。 行至一地,看到景区说明,以为此花便是其介绍的“美丽胡枝子”了,待到歇息时,我手机查看相关内容,一对比,花期不同,花形迥异。胡枝子在7-9月开花,这样看来我还是认错了,这花儿于我而言应了这句话:养在深闺人未识。 世上的花儿无数,我不识的花儿亦无数,也不差这款白花。及至第二天上山会合的小伙伴里,有人指出:这白花儿是杜鹃花。她的话颠覆了我长久以来的己见:杜鹃花就是红色的。 南唐诗人成彦雄有诗云“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尽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看来至少唐宋以来,就有人认为,杜鹃花以红色为主流、为正宗。在现代语境中,杜鹃花更应该是红色的。杜鹃花由革命者的热血染成,象征着革命之花、红色文化之花,再说了杜鹃俗语不就是《闪闪的红星》潘东子歌唱的映山红么?若是白色,岂不是成了映山白?政治不正确呢。 看来,我的植物与花卉知识太贫乏了。于是补课了解杜鹃花的前世今生,才明白杜鹃花的五颜六色,有红、淡红、杏红、雪青、白色等。 杜鹃的别名有:杜鹃花、山踯躅、山石榴、映山红、照日红、唐杜鹃等。在一衣带水的东邻,人们称其为踯躅,它泊来自我大唐盛世。 杜鹃花记载最早见于汉代《神农本草经》,书中将“羊踯躅”列为有毒植物。杜鹃花栽培历史,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白居易对杜鹃花情有独钟,写出赞美杜鹃花的诗句,如诗曰:“忠州洲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年树,已怜根损斩新栽,还喜花开依旧数。”据记载,唐贞观元年已有人收集杜鹃品种栽培,最有名的是镇江鹤林寺所栽培的杜鹃花。 宋朝曾巩有诗《杜鹃》 杜鹃花上杜鹃啼, 自有归心似见机。 人各有求虽意合, 何须勤苦劝人归。 宋朝何应龙有咏《杜鹃》 君若思归可便归, 故乡只在锦江西。 不知何事留君住, 却向空山日夜啼。 据说杜鹃的叫声,在文人骚客听来乃“不如归去”,是劝游子返归的。本人此次返乡祭祖,顺游三清山,听杜鹃啼鸣,似乎我也听从了杜宇的旨意。 李白见花起相思,触景生乡情,其诗云。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诗文将花与鸟联结一起,自然想起同名杜鹃鸟来。对于书面语的“杜鹃”,无论其指花还是鸟,于我都很隔膜,甚是惭愧。在很长时间里,我未知杜鹃鸟是何方神圣?它有着怎样的形象?后来才知道,它其实就是故乡土话所说的咕咕,学名叫布谷鸟,才恍而感叹,原来就是它呀。 网上查询词条:布谷鸟别名杜鹃、杜宇、子规、鸠、鳲鸠、又叫鶗鴂、鷤?、子鹃、蝭蛙等等,还有一个别称,叫杜宇。有诗为证。 忆王孙·春词 [宋]李重元 萋萋芳草忆王孙, 柳外楼高空断魂, 杜宇声声不忍闻, 欲黄昏, 雨打梨花深闭门。 布谷鸟的名字, 次出现是在郭璞的《尔雅注》里。在此之前,大多称它为“鸤鸠”。但根据史籍记载,布谷有许多别的雅号,有“桑鸠”、“击谷”、“郭公”、“割麦插禾”、“阿公阿婆”、“郭嫂打婆”、“一百八个”等二十多个,大多数名称模拟于鸣叫声。 这些名称,与我家乡说法相合。家乡到底是叫咕咕呢,还是谷谷呢?论口音前者更接近。小时候,我和母亲在地里干活,听到布谷的叫声,母亲就现行说法,她讲布谷说的是“各家各户,割麦载禾”,谐音确实相同。母亲说,布谷一叫,春天就来了,农忙便开始了。在南方家乡,我们割冬小麦,插的是早稻,这二件农事相连,就如夏季的“双抢”一样。 然而,至今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家乡有二种鸟儿,我从来是只闻其声,未见其鸟。一种是布谷鸟、即所谓杜鹃的,还有便是一种水鸟了。 这里讲一段题外话,与杜鹃无关,讲讲这种水鸟。在南方早稻成长的季节,在田坂里,这鸟儿能够激发出巨大而特殊的声音,单音节。直觉不是鸟鸣声音,而是水鸟用脚蹼儿击打水面发出的拍水声,“潡、潡、潡、潡……”个不停。曾有几回,我在稻田里耘禾,从隔垄水田传来潡潡潡的声音,我放下农具,学着 匍匐前进,悄悄地接近它,我并非想捉住它,只是想看看它的模样。这种水鸟很狡猾,它也不飞,待我靠近,它便停止叫声,我就找不着北了。等我悻悻离去,又开始了它的发声。 为此,我回家问长辈。大人说,这个水鸟,声音虽大,身体却小,而且精灵,你哪里能看到它呢。世上有些东西,真是身小声大、人小鬼大,黔之驴大。 杜鹃鸟儿(我还是习惯叫布谷鸟哈)也不例外。春天里,到处可以听到它的叫声,可我从未近见它,它飞在高高的天上鸣叫,看着比麻雀还小。其声如雷贯耳,其身飞龙在天。令人联想起历史典故,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杜鹃乃是久闻其声,未见其“人”的世外高鸟了。 布谷鸟如神一般的存在,一提起它人们都知其声,但要人说出它的模样,很多人未必见过真身。村里的阿文表兄抓过斑鸠,我是见过的,但人家说斑鸠并非咕咕鸟,那么我就真没见过杜鹃鸟了。 这回我在三清山,又听到了“布谷……布谷……”的声音在海拔千米之上的山巅回荡。它的“Cuckoo”叫声,令我想起了一首诗来。 THECUCKOO InApril, Comehewill, InMay, Singallday, InJune, Changehistune, InJuly, Preparetofly, InAugust, Gohemust! 只是我不明白,老外为什么要将杜鹃叫HE而非SHE呢?这大概也是中外文化差异吧? 但若深入了解杜鹃习性,我被告之杜鹃并非好鸟。滥情不贞、借巢孵蛋、摔杀同袍。这样的鸟族劣性,以雄性形象指代之,似乎更恰当。试想,在动物界,有哪个母亲不疼自己孩子的,居无定所、生而不养,这不是女性、母亲的特点,更合乎部分雄性滥情而不顾家的劣性。民间有句话,“宁要讨饭的妈,不跟当官的爸”,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如今我也是孩子他爸了,只是没有当官,孩子也还是跟妈也跟爸的啦。时光匆匆,一晃已是新冠疫情之后的第二个春季,政府在节前放开了跨省旅游,让我得有此次故乡之行,倍感珍惜,感慨万千,想起了李商隐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人生倏忽,转眼五十弦了,这次来到故乡补课, 次登上三清山,我就被故乡的锦绣江山所震憾。三清山的杜鹃在鸣叫,山腰间路边的杜鹃花也开了。可是玉清台前的杜鹃坡、杜鹃谷的杜鹃却不见花开,大概是此处坡谷的海拔更高、气温更低吧?不知道杜鹃坡谷里杜鹃花盛开的时候,满山呈现什么颜色?应是映山红吧? 往后的春天,我得掐着时间来看看三清山的杜鹃谷、杜鹃坡、还有那一片千年杜鹃林、甚至那一颗杜鹃王树。我要看看满山坡谷盛开杜鹃花儿的世界,那时的故乡该是如何如火如荼?或者冰清玉洁? 改 DOSEEING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juanhuaa.com/djhzy/8533.html
- 上一篇文章: 演员杜鹃与MeltingLightl
- 下一篇文章: 沁园春哀牢杜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