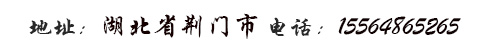浙南有个岩背村山石草木情缘6
|
浙南有个岩背村:山石草木情缘(6)(-06-:49:53) 此草含情 说到山区,总是山高路险林深苔滑,普通山自然也是这样。然而你深入它的底部,登上百丈崖岭,便把黑黝黝的石头,莽苍苍的林木抛在后头,眼前豁然开朗了。这里群山起伏,山势和缓,山色柔嫩。环抱中的岩背村,清新明朗。环村是松竹,稍上些的鸛鸟尖、山马垅、天帽尖、马草坪、青山岗等,便整个山头整个山头全是油亮油亮的青草,偶尔也夹杂着大片的灌木丛。一年中的春夏秋三季,天女不断把花撒下来,白似雪,红似火,粉似霞。其中尤以春季的杜鹃花为最,那是成片成片地开放,接连几十上百个山头,把青山绿水涂染得分外艳丽。秋季的花即是星星点点的,油亮的阳光给黄绿山坡镀上了一层金色。此时此际,不但花是这样艳丽醉人,而且你还可以享受到丰盛的野果大餐。因为春花所结的果实已经成熟了,村人们可是成担成担地采摘呢! 当然,此事前文已述,在此不必赘言。这里要说的是秋冬以后,灌木落叶了,山草枯黄了,普通山上的又一道风景:放火烧山。 倘在冬间,那大多是不经意点的火:或者是磕下的烟灰引起,或者是野炊的余火复活,或者是野孩子的玩火游戏造成。开春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田地山坎的茅草是必须去除的,否则就成了鼠雀的乐园,庄稼难免遭到损害。而且最主要的是,经过放火烧山,明年的山草才能旺发。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化肥,即使有了也用不起,而且村人也不大相信,说用多了肥田粉,土地要结板,不如山草现成,又能发田。所以每年吃过立夏饭,人们便上山割草铺田。铺了田还要铺地,铺得黄土不见天,既当肥料又保土,杂草不得生,天旱也不怕,玉米番薯呼呼往上长——所以放火烧山就是故意的了,在岩背,放火烧山绝不是破坏,而是一项重要的生产建设呢!当然在仙居就不行。可是交界村庄,历史上割树叶从来就不分地界,仙居草山也要放火才好呢?于是就有青年乘夜在边界的山岗之上,将“火鸟”飞到仙居山下。不一会,就传来山下呼呼的大火声,他们这才拔腿逃回自己的山界内。 想想看,这一个晚上,该会烧去多少荒山?这场面,这阵势,该有多么壮观?山里人将它比做正月十五闹龙灯,其实比之闹龙灯又何止千百倍?且看火势不断蔓延,眨眼间四周的草山一齐腾起烈焰,形成无数条火龙在山间舞动。呼呼呼!风助火势,火龙呼啸着又扑向另一个山头。随即一而十,十而百,不知几十几百,在连绵的群山间舔舐、奔腾、穿插,夜晚时连整个天空都被烧红了! 在放火烧山时节,村人们总爱坐在门头,一边吃着晚饭,一边看着火烧山。但他们谁也不会问这火是谁点的,自然更不会有人提出前去扑灭,除非是威胁到了近村山头的林木。总之,这样的大火可以烧到几天几夜,最后究竟是怎么熄灭的,也不会有谁去过问。于是万千大山一概披上了黑甲——一层厚厚的山灰。春风吹,春雨下,灰汁滋润着草根根。天气一转暖,草箭儿就死命往上拱,随之就蓬蓬勃勃生发起来。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哪! 经过大火以后生发的山草,村人们给它起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火烧”;但大火也会留下死角,这就是“老蓬”了。 在山草的生发时间上,“老蓬”要比“火烧”早许多。“老蓬”是在各工鸟,也就是杜鹃鸟的一声又一声的催促下开始抽枝拔叶的。一段时间后,“老蓬”新枝变旧条,“火烧”才开始旺发起来,各工鸟也随之来到火烧山。所以,普通山的山山岭岭就仿佛是各工鸟叫绿了似的。 这样的描写是历史的,因为放火烧山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被绝对禁止了。 这样的描写是诗意的,因为化肥的普遍使用,已经很少有人上山割草了。而所谓诗意,多半是旁观者的专利,实践者却大多没有这个闲心。他们所感受到的更多是辛苦,甚至是苦痛。 上山割草,村人也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割树叶”。那是农民们给农田施底肥,具体操作要求是:先犁好田,稍作平整后,将树叶深深地踩入泥里,时间必须抢在插秧之前完成。岩背村水田不多,每人平均不过五六分,但要一丘丘全铺遍树叶,任务却异常繁重,其持续时间竟然长达三四十天。就全年活计来说,其重要性、艰巨性,无疑都是“重中之重”。因此,除了读书的孩子,还有裹脚的老太婆,村人几乎没有不上山的。 割树叶是很辛苦的。就说“老蓬”吧,因为原有的柴草基础没有受到破坏,荆棘遍布是不必说了,因而真正的岩背人,没有谁不是伤痕累累的。在诸多伤痕中,刺伤比例十占其七,其余三成为刀伤。而“老蓬”的真正危险却是野兽经常出没,只要进入纵深地带,遇上野猪是经常的事。其实野猪并不可怕,因为即使遇上了,它也不会主动发动攻击。若说可怕,那就是老虎,二水伯就曾经遇到过,幸而四周的人闻讯前来声援,否则连性命都没有了。 要说割树叶,无论怎样都是辛苦的。晴天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可人们得天一亮就上山。高山露大,“老蓬”柴多,露打衣裳半身湿。到了中午边,依靠暖烘烘的太阳,还有暖烘烘的体温,上身衣服才烤个半干,下面裤子却还如水里涝上来一般。而割树叶的日子,总是以雨天为多,在老蓬山,便是带了雨具也难以用上。只是用不上也得带,后生人不愿带,老年人可得带,因为他们已经感到湿气攻心的厉害了。平平村人最好的雨具是蓑衣,而这却不是人人都有的,一户人家能有一领就算不错了。这是用棕片制成的,棕片市价每斤四五角钱,制作一领需要20来斤,请棕匠要四五天,总计下来要20来元钱。所以你要带蓑衣,还不定有这个福气呢!女人和孩子是决没有这个福气的,他(她)们只能带箬帽。而在老蓬山,箬帽的功能最多也只是护卫头发;至于上身下身,前胸后背,衣袖裤管等等,都只有照湿不误。尤其糟糕的是大雾天,那简直连头发也护卫不了。因为在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之上,浓雾如雨,雾雨难分,混混沌沌,绵绵密密,无论蓑衣箬帽,一概派不上用场。而且这雾湿,与雨湿又自不同:雨湿还有外湿内干的区别,而雾湿却是内外高度一致,虽然拧不出水来,却是湿皮湿骨湿心湿肝,天长日久,不湿出你一身毛病才怪! 在诸多受害者中,老人如老牛般的喘气是最突出的,当然也最让人同情,因而队长便有意安排他们犁田。然而他们却问:“每天记多少工分?” “按老规矩,(每天)12分呀!”队长说。 队长说的是在割树叶期间。要在平时,田里活可只能记10分,因为他们只有8个底分。 对于这12分,老人们可要好好算计一番:上山割树叶虽然辛苦些,但一天可以挣个十四五分,比犁田要整整高二三分呢!再说犁田就不辛苦吗?天一放亮,就得赶牛吃草,这时候割树叶的人也才起床呢!而且犁田这活儿复杂,牛有耕脚好坏,田有老嫩分别,无法按件计酬,犁多犁少,众人就免不了七嘴八舌——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这犯得着吗?还不如上山割树叶呢! 于是他们就不领队长这个情了。 现在是割“火烧”,比割“老蓬”要好许多。老人们去不了远山,作伴的还有几个孩子,那是严厉的父亲逼着他们“锻炼”。老祖母尽管心疼,却也不会反对,因为早年她对儿子也是这样进行“锻炼”。山里孩子谁不是这样“锻炼”出来的?只是近山的树叶没有远山的茂盛,稍长些都长在乱石堆旁。这样的地方,刀一碰石头,就“当”一声反弹。孩子肉嫩,“扑落”一下,半截指头就掉到石罅里去了。即使幸而沾着一层皮,也是满手鲜血,吓得孩子哇哇大哭。老人闻声而至,便摘下几个蕨薇芽头,嚼烂敷在伤口上。血总算被止住了,但手上便永远留下了一道伤疤。这是刀疤,比刺疤严重多了,据说长大以后飞行员就当不成了呢! “火烧”草短,捆绑又成为难事,串连成担尤其困难。山里孩子都很好胜,他们不愿让老人过来帮忙,于是便自己想办法。常见的结果是串担失去平衡,一捆树叶从陡峭的山崖滚了下来,其势如车轮飞动,速度越来越大,“车轮”则越来越小。倘若中途有树,还有可能搁住,否则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滚没了。于是孩子的哭声再次而起,这回连老人也没有办法了。孩子则一边哭着,一边收拾。收拾结束,眼看只剩下一小捆了,孩子的哭声止不住又起…… “各工!各工!” 各工鸟又叫了! 叫声在高高的山崖之上。那是它在提醒孩子,那里还有一捆没有滚下的树叶。那么是将它也滚下来呢?还是将眼前这一小捆呼哧呼哧背上去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ingchong.com/djhyf/2487.html
- 上一篇文章: 罗湖八层楼高的ldquo勒杜鹃瀑布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