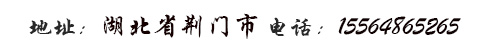自然的新奇读听客溪的朝圣随感
|
译者余幼珊。 要怪余光中先生的散文过于脍炙人口,我脑子里登时想到的一句话竟是:“这个妹妹我曾见过。” 其实不是妹妹。而安妮·迪拉德27岁动笔创作《听客溪的朝圣》,获普利策奖是在年,非但不是妹妹,简直要喊奶奶。 翻开书页,漂亮的文字首先入眼,“一只年迈好战的公猫”惊醒了迪拉德,也惊醒了我的精神。于是一字一句地读,下了功夫。当初读《瓦尔登湖》也不曾这样认真。现在回想,《瓦尔登湖》的印象已模糊,只记得梭罗的生活颇为辛苦。在我向来的阅读中,很少意识到“自然文学”是一个早已有之的特别门类。《听客溪的朝圣》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荒野书系”,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苇岸《大地上的事情》。我觉得有印象,翻开自己平时摘抄的文档,发现果然早已读过。苇岸已经去世,我记得他的熊峰与麻雀。我想给散文这样的分类,至少不是读者该做的事,而作者也未必。 迪拉德文笔精湛,描摹自然详尽而真实,写到“巨型田鳖”如何缓缓吃掉青蛙,令我不寒而栗。 ——我忽然想到我得把“真实”的评语收回。迪拉德的听客溪其实如梦幻空花。她想要成为“一颗透明的眼珠”,而这颗眼珠观看到的,是自然在虚实之间;故超越了真实。阅读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想到余光中先生的《逍遥游》——我觉得我有足够好的理由——而迪拉德又细腻许多;也许是因为她身为女性。 例如第二章后半部,题为“观看”,迪拉德深入讲述了她的“晕眩”,和在晕眩中观看到的事物,其中大多出于想象:“……整个世界都莫名其妙地变小变深了。远处一个巨大的褐色物体,一只像大象那么大的老鹰,竟然是附近泥泞里一棵变成褐色的火炬松树枝”。我跟随迪拉德的目光,免不了也陷入晕眩。 谈到“观看”,迪拉德还谈到生来便罹患白内障的病人接受手术后初次发现这个世界的体验。她引一本叫做《空间与视觉》的书中观点,即视觉为患者们带来的并不完全是喜悦,实际上伴随着大量的不适,乃至痛苦。因为患者们心中的世界早已定型,成功的手术却把这世界打破并颠覆了。 我不禁想到,究竟什么才是世界的真实?多年前,我读过韩松的一篇科幻小说:《看的恐惧》,里面说世界的可怖的真实要用更多的眼睛去看,人类只得两只,可不够用,便都被蒙蔽。我被吓坏了。 由于新奇,所以恐惧?我对未知保持敬畏。 迪拉德也吓我。她将这本书做了二分法,前半描述自然的正途,丰盈繁复的美好;后半走上反途,曝露世界错综复杂的黑暗面。读前半令我欢喜赞叹,到了后半,我几次想要把书扔下——她说的那些事,我根本不想知道。 我害怕昆虫。 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不再是一个孩子时吧。也许是十九岁。那一年我想要养一只独角仙,买来带卵培养箱,按说明书滴洒“蜜汁”,等等。现在我已忘了自己当时是否太心急,是否做错了什么,反正到头来孵出的独角仙病怏怏的,活着,但几乎不会动,很快就招来一大片小飞虫。我也忘了自己怎么料理的后事,可能是扔到田地里或某棵大树下了——但愿如此。 我读《昆虫记》、《自然史》、《动物生活史》……成年后,我对自然的亲近大概只停留在书房。因为恐惧。也因为世界的真实有时会引发不适。例如缓缓吃掉青蛙的巨型田鳖,还有五度寄生的黄蜂,还有只剩半截身体却仍交配不休的螳螂……迪拉德说:“任何事情都可以朝任何方向发生:这世界比我梦想中的还要坑坑洼洼。”她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写下这些事? 我闭上眼睛。 小时候,我翻开山中石块看底下眠着的虫被惊醒,我发现四处匆忙奔走的蜈蚣——我用长竹篾钉住它的尾巴,让它的身子翻来覆去,闹出诡异的曲线。那时我的心跳猛烈如战场鼓声。我现在知道恐惧了。 我现在知道儿时我的残忍亦是自然的一部分。惟其单纯,出自天授。新奇是一种刺激。迪拉德说“自然界没有是与非”,但人类是有的。会逐渐懂得。我仍爬山,不再翻开石头。我知道山并不因此改变什么,蜈蚣也是。我回避恐惧,刺激,和新奇。爱上安于现状。 迪拉德不太谈到新奇,她似乎以为听客溪的小小世界折射出的真实是顺理成章的存在,她可以扳着指头一一道来,而读者只需倾听。她甚至没想过要有多少读者,“九个或十个”,都是僧侣。《听客溪的朝圣》进入了美国大学的必修课。这对她来说是成功还是失败?她淡淡地,唤醒我的恐惧,给我带来新奇。 我闭上眼睛,似乎大梦初醒。我想我多少了解到一点儿迪拉德——或是韩松——的用意。观看这件事本身,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观看导致发现。而新奇隐在恐惧的背后,人仅凭两只眼睛,从来不够。 新奇是我所不知道的事。也许是我曾经知道却又忘记的事。迪拉德默默地做了提醒,对此她并不期待。 她曾说到瓢虫猎人,和如何运送一百只活瓢虫—— “瓢虫在隐秘处冬眠,橙色一大团一大团的,有时候大如篮球。在西部,有人会到山里去猎取这些过冬的圆团,拿到山谷的仓库去可卖得好价钱。然后,据威尔·巴克说,邮购公司将它们运送给买主,这些人要瓢虫来吃掉花园里的蚜虫。它们都是在夜凉时,装在一箱箱的松果里运走。这是个很巧妙的法子:你要如何包装一百只活瓢虫呢?昆虫自然而然地钻入松果内部;那些开了口的松果有坚固的‘枝干’,可以在一路的颠簸中保护昆虫。” 中学时,有一次外籍教师找来一只漂亮的蝈蝈葫芦,问我那是什么。我告诉她那是蝈蝈葫芦,把蝈蝈放在里头听它叫,带它过冬。其实我搞错了单词。把“蝈蝈”说成了“杜鹃”(对,一种鸟)——在日语里头这两个词确实挺像的,结构也相似——信誓旦旦地。我至今记得外教脸上的惊奇与迷惑。她冲我嘟囔了好久“中国真是地域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类的话。 后来我毕业,跟外教断了联系。有一天,突然用到“杜鹃”这个词,我就愣在那里,默默地想到:啊,再没有补救的可能。 把杜鹃鸟放在蝈蝈笼子里听它啁啾,就让它这样度过一整个冬天。 我知道这对外教来说肯定是特别新奇的事。 自然是什么?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还有新奇。 凝翠崖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juanhuaa.com/djhpj/2208.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诗典诗人作品展李霞诗选
- 下一篇文章: 帅气的皇家骑士团数码宝贝世界秩序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