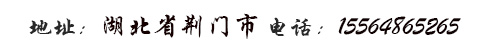作者刘锋阳台趣花木宠物系列感悟
|
四、禽鸟的乐趣 刘锋 “杜鹃啼,鹦鹉诵,刺猬变球戏鸡公,乐煞田家侬”。 ——思啸题记 (二十四) 古人买山退隐,耽于林泉,自有一番淡泊的清趣。现代人,居于繁华都市,房屋密得如同蜂房,楼宇高得似可摘星,那“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幽篁深掩的境界,似乎已经难再了。但是,现代楼房,配上现代阳台,巧妙地利用好那块方寸之地,回到田家去,与那禽鸟融融相处,去品玩那鸟儿身姿的怪状,去猜度那家禽语言的奥秘,去欣赏那鸟儿舞蹈的美态,去陶醉那家禽歌唱的乐韵,去领略那田园生活的欢乐,那可就是另一番趣味了。 “喔——喔——喔!”东方刚刚吐出鱼肚白色,人们还在春眠中酣睡,我外甥晓坤寄养在我家阳台上的一只雄鸡,已是先人而起,用它那嘹亮的歌喉,负起了它司晨的职责。 这晨啼,是破晓的乐音,愉愉快快地,绕过苟骨树,飘上木槿花,沿着葡萄的藤蔓而旋升,余音回环,不绝于缕。 晨啼,荡漾出了一个愉快的氛围,那葡萄架下挂笼中春睡的红嘴绿鹦鹉醒来了,一对玲珑娇艳的小夫妻,把桔黄色的小脑袋探出白墙红尖顶小屋的门,东瞧瞧,西看看,“呀,该起床了!”不知哪位用鸟语叫了一声,笼中就顿时热闹起来。 小夫妻夫唱妇随,前后相接,钻出小屋,这个立在笼中的横木上,整羽毛,理新妆;那只歪歪头,煽煽尾,袅袅娜娜地摆动着娇小的身姿;一会儿又你三蹦,我两跳,用喙勾住横木,旋上去,寻寻那快乐的声音,用爪圈住钢丝笼的直杠,溜下来,玩点稀奇,给那司晨的“什么”瞧瞧。 “啾啾叽叽”,不一会儿,这对小夫妻放肆地把那浑身雪白,雄纠纠,气昂昂的雄鸡打量了一番,轻声议论起来。 “嘘,小声点,别把那位忘情歌唱的鸡哥惊了!”那只用爪抓着笼格偷眼斜觑雄鸡的雌鹦鹉,低低地哼了两声,好似在说。 “噫,那买弄嗓儿的‘骚哥’,还靓得很呢!”用脚勾着横木倒悬着的一只雄鹦鹉,扭头对着雄鸡眨巴着眼,抿着嘴暗笑着,用神态传达了它那内在的语音。 “吓,这处书房真大,那里居然还睡着那个‘书呆子’,他正在梦中,屁是屁,鼾是鼾的,怎么春睡这么迟迟?”那反身贴着笼格,悄悄侦探书房动静的雌鹦鹉,眨一下眼,向房内瞄一瞄,“啾啾……啾啾”,连续叫了十几声,俨然在那里嘲笑。 雄鸡抖抖雪白的羽毛,跳上了栽种苟骨树缸沿边向下斜伸出的一根硬枝,以更亮的嗓音,歌唱起来。 这歌声,亮亮的,撩得那对鹦鹉夫妇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心跳不以,它们争先恐后地对着雄鸡和书房发出了温柔缱绻的声音:“啾晰,啾晰,啾晰……”那分明是在唱:“鸡啼,鹦叽,书房里的‘呆哥’,你乍还不起!快快早起,还不快来享受这快乐的阳台春!” (二十五) 阳台上,鸡啼嘹亮,鹦唱委婉,那飞荡的音符“豆芽菜”,伴着露珠,跳跃着,它蹦进了我那阳台通向书房的漏窗,使初醒的我,心中充满了快乐。 禽乐声,让阳台风致起来,假山,它透出了朗润的颜色,碧泓,也泛起了清秀的涟漪,植物叶片上,露水滚动着,刚刚绽开的花儿,半遮半掩,慵绻中含着娇羞,今天的阳台,肯定乐味无穷。 苟骨枝上,响着那田家生活的乐韵,那只自我陶醉的“骚哥”,正精神抖擞地压尾挺胸,引颈昂首向上,目不斜视地庄严啼叫着。 它叫一声,歇一下。叫时,“骚哥”神情异常专注,好似那世界上的一切,都溶化在那叫声之中。歇时,“骚哥”就换了一副神态,左一顾,右一盼,用爪搔搔树枝,又夹着翅膀,移动几下脚爪,然后,向左偏过脑袋,对着宠物精舍半圆形的拱门,不停地摆动着那通红的冠子,斜睨着,看那舍中苕头憨脑的怪种狆狗,鼻子是否皱了起来。稍稍一会儿,它又将眼光瞟向宠物精舍旁的一个刺猬洞口,把头压得低低的,偷偷地窥伺那洞口露出的尖嘴猴腮相,瞧那上面神秘的小眼睛,有没有闪出一团顽皮的光。 阳台上,没有都市的气息,却充溢着那田园生活的快乐。方寸之地,到处一片葱绿,花开着,鸡啼着,鸟啭着,刺猬蠕动着,狆狗懒腰伸着。 两只半大的雌童子鸡,拍拍翅膀,蹦出窝,显示出了它们童稚的乐趣。那浅黄色的绒毛,刚刚换上一身杂色的羽翼,与那雄鸡漂亮的羽毛相比,像极了小叫花子和绅士站在一起,不免使童子鸡显得太寒酸了。那童子鸡幼小时则为清一色的嘴脸,而此时也开始有了区别,显出了个性。那屁股上随时拉出的屎,让洁净的阳台上,颇有点儿脏眼。这就仿佛是那牙牙学语,鼻子上挂着鼻涕龙,屁股上沾着屎浆的幼儿一样,自有让人乐不可支,又有使人生厌的地方。 小鸡出笼,让“骚哥”快乐起来,因为那是两只已有点显出线条美的童子鸡婆呀!“骚哥”“骚”趣顿生,快哉,乐哉。 童子鸡婆姗姗一出,“骚哥”眼光就立马发直,只见它拍拍翅膀,抖一抖那雪白的羽毛,甩动几下那足可以炫耀,有两寸高,又大又厚的大红冠子,然后轮换着慢慢缩起它那有精有神的腿,再非常有力地猛然踏下去,伸动着脖颈,四平八稳,昂首阔步,展示起雄姿来。 “喔咕——”“骚哥”仰起脑袋,本想发出美妙的一啼,用以显显自己“骚”的性别和个性。不想它太激动了,使喉头发哽,那一声响,竟是变了调成为阴阳怪气的嗓音。 “骚哥”见毫无动静,就低下了头,“咯咯咯”地轻唤了几声,示意那两只鸡婆快点过来。 那两只鸡婆,此时正在鸡笼旁边快乐地打逗着,那样子,就好似阳台上毫无“骚哥”踪影似的。 “这还了得!”那“骚哥”不禁生气地翻起了眼球,脸颊上的冠子肉一阵发白,它以左脚为圆心,在原地打了一圈。 “岂是我自作多情,谁不知我是阳台有名的‘骚’怪?”“骚哥”想了想,终于压下性子,又换上一副媚气的样子,装做找到谷子似的,把鹦鹉从笼中抛下的小米壳儿,拣起来,丢下去,丢下去,又拣起来,一边闪着流氓眼,一边“咯—咯、咯,咯—咯、咯、咯”地哼着黄调调,斜“挲”着翅膀,旋了半圈,用那花花动作,去撩“骚”那只尚分不清“男女”的鸡婆。 面对着“骚哥”的煽情,懵懂的雏鸡茫然地望着,“叽叽叽”地直叫,以为那“鸡纳叔”是在抽筋。那两只童子鸡婆也是实在小得看不懂“骚哥”的黄色动作,一个作奇怪状,歪起脑袋,“啾啾”急叫两声,疾呼“发鸡瘟啦!”一个自顾自地用那尖尖的鸡爪,在光溜溜的地砖上,无目的地扒着,对“骚哥”的呼唤充耳不闻。看着这大相异趣的鸡态,真可让人捧腹。 (二十六) 太阳爬了上来,给小小的阳台带来了融融的暖意,惯于夜生活的刺猬,此时一反常态,兴许是出于玩“骚”的乐趣吧,竟贼头贼脑地从洞中钻了出来,它轻巧巧地顺着阳台的墙边,用尖尖的嘴,铲着地皮,朝前移动,贼溜的小眼,窥视着“骚哥”的骚样。 这只刺猬的脑壳,活像一个小小的鼠头,那溜溜的眼珠,闪着难以琢磨的光芒,尖尖的嘴里,哼哧着,它几步溜到苟骨树下,用古怪的眼神,瞟着那带刺的狗骨形树,嘴唇咧了一下,像在戏谑:“哟,你的刺多,可以叫‘鸟不宿’(苟骨树俗名鸟不宿),我的刺长,是否可叫‘骚鸡怕’?” 也不知这只刺猬是乐在鸟不宿,还是乐在骚鸡公,它看看苟骨树叶,又斜眼瞅了瞅“骚哥”,鼻子两边晃动着。 不想无意间,刺猬的鼻子突然被那苟骨树叶上的刺给锥了一下,“哧!”刺猬生气地用鼻孔对着苟骨树喷了一下,向后退了几步,打量了一下苟骨树的茎杆,然后挺起满身如同钢针长刺的脊背,向着苟骨树的茎和叶撞去。 “啪!”这一撞不打紧,苟骨树只是轻微地动了一下,倒是把那只欲火如焚,身子一耸一耸的,正在连续做着更下流动作的“骚哥”吓了一大跳。那“骚哥”收起了色迷迷的眼神,停止令刺猬快乐的“挲”翅、打圈、凸背的淫秽动作,把头低了下来,眼中冒血,竖起了脖上的翎毛,“挲”开双翅,蓬起全身的羽毛,增大身体的空间体积,用那尖尖的喙,瞄对着刺猬的小眼睛,怒视着,恨不得吞下刺猬。 这只刺猬本来就是为“骚”乐而来,它见“骚哥”收起了“骚”相,就嘴角咧动,暗吞着笑,然后抬起小脑袋,向后退了两步,身子一前一后地摇动了几下,学着“骚哥”的黄动作,鼻子里“哧哧”有声,喷出了调戏的气来。 “骚哥”狂怒了:“狗东西!老子鸡群中从来不兴‘扫黄’,要你来管‘骚’闲事,冲了我的兴致。”“骚哥”颈子骇然挺硬,羽毛徒然直竖,两喙急速张合,脑袋伴着刺猬的“扫黄”动作而频频点动,眼光凶狠地盯着刺猬,喉咙里“咯咯”有声。 “汪!”那狆狗在宠物精舍中,突然对着“骚哥”大吼一声,鼻子发皱,上唇提升,露出了凶猛的犬牙,那神情非常明显:“真是‘骚’得有瘾,你们扯皮,怎么惹到我身上来了,还骂什么‘狗东西’!” “骚哥”未防腹背受敌,本能疾速地腾空而起,由空中向下,对准主敌刺猬的眼球,狠命地啄去。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时,刺猬以闪电般的速度,低下脑袋,缩起四条小腿,迅速卷成一个刺球,用尖足拨动着阳台的地砖,滚移着,步步为营地稳扎稳打,采取地对空的战略,迎战着“骚哥”的空袭战术。 隔着阳台与书房门上的亮窗,看着阳台上的“骚”斗,听着“骚哥”高八度咯咯声和它翅膀的噗啦声,我快乐得手舞足蹈,急喊妻女快来看。但同时,我心中又在隐隐着疼,不就是几个自然界中的“骚”动作吗,那刺猬也是撩得太凶,把“骚哥”的鸡冠都刺得流血了。 看那刺猬还不肯收手,为了解救“骚哥”,我猛地拉开了门,对着刺猬大吼一声。这突然一吼,倒是把刺猬给“镇”住了,那灰色的刺团子,立即停止了滚动,没有了动静,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看到,那刺球又蠕动起来,慢慢地伸开身子,从刺丛中伸出小尖嘴,两个小眼球怔怔地望着我,打量着。那只“骚哥”呢,也非常灵活,就在我开门的一瞬间,它如同见到救星似的,一拍翅膀,猛地飞到我的肩头上,借着主人与刺猬的“块头”悬殊,“咯咯、咯咯”地叫个不停,一边威胁着发楞的刺猬,一边“骚”得快乐无比。 就这样,那刺猬与我静静地对峙了一会,才突然一个急转身,翘起屁股,对着“骚哥”一摇身体,然后小跑着,奔回它的掩体洞内,躲这吓刺猬的“一吼”去了。 (二十七) 我见阳台静了下来,就进入了客厅,但那“骚哥”却一直就站在我的肩头上,并没有下来。我把它往下推,它仍然不肯下,喜欢与禽同乐的我,也只有任着它了。我在原地转了几圈,见它仍无下来之意,于是,就就便坐在了沙发上,“骚哥”见状,也在我的肩头蹲伏了下来,并时不时地将它的脑袋并鸡冠,在我颈上磨蹭着,又用它的喙,帮我理理头发,算是谢了我的救命之恩。 这一天,正好是双休日,双休,不仅意味着我们全家有阳台乐,而且那阳台上的禽鸟们,像是专等着这一天似的,也与往常格外不同,乐趣倍增了。 因那只雄鸡寄养在我家,为此,晓坤就隔三岔五到我家来,陪着“骚哥”玩耍。他可是特别喜欢动物呀,更是喜欢“骚哥”,视“骚哥”如命啰。这样一来,晓坤每次来到我处,都要教它如何迎客、送客、看电视,并与它打足球同乐,甚至连做作业时,都把“骚哥”放在两腿中间。而那只“骚哥”,则在晓坤两腿上,向两侧伸直两爪,“摊”着个“一”字,并用嘴点着晓坤的作业本,装着学习写字的样子。为了“骚哥”的健康和掌握它的习性,晓坤和我女儿偲偲,还特地为“骚哥”建立了一个档案,他们用观察法,将“骚哥”的吃、住、行、玩、睡、骚,一一详细记录下来,这样,久而久之,竟也记了一大本。 那“骚哥”呢,也非常通人性,特别钟情于晓坤,时时等着晓坤的来临,时间一长,它也几乎掌握了晓坤的规律,每到那个愉快的等待时刻,“骚哥”必然要蹲到客厅正对大门的煤气罐子上,耳朵竖着,眼光闪着,随时捕捉那楼道由远而近传来的熟悉脚步声。 “唰”,刚才还在我肩膀上无限亲昵的“骚哥”,此时,突然站了起来,一下子飞到煤气罐子顶上,它在那里伸头,抬腿,激动异常。我们大家都明白,准是晓坤已上楼了。 女儿见状,忙将客厅门虚掩着,不久,“咿呀”一声门响,我还没站起身来,“骚哥”就“咯咯咯哒”地叫个不停了,那是一种鸡婆生下蛋后的叫法,在于“骚哥”,则是以此叫声来“装靓”呢。跟着,那“骚哥”又呼地一声,向大门飞去。待我抬头看清时,真是一点不错呀,正是晓坤来了。只见走进客厅的晓坤,一手抱着“骚哥”,一手在摩娑着“骚哥”足有一元钱硬币大而又通红的下冠子,那“骚哥”此时的样子却嗲嗲的,半闭着眼,在晓坤怀里忸怩作态,将小脑袋直往晓坤衣服里钻啊。 见此情状,晓坤走到客厅墙角,伸手在茶几下层托出了一个足球。“球!”那“骚哥”一下子兴奋起来,赶忙把头从晓坤衣服里钻出,眼睛瞪得老大,身子贴在晓坤怀里,向前倾了倾,用那坚硬的喙,勾着晓坤手中的球,向外一拉,只听“啪”的一声,那球应声落地。 那“骚哥”的小脑袋,随着球跳而点动,球弹起,“骚哥”的脑袋扬起,球落下,“骚哥”的脑袋倾下,待球跳快要停下时,我提起一脚,将球踢向阳台。 这一踢不打紧,把阳台上正在晒太阳狆狗的球瘾惹发了,它嘴里“骨努努”地发着喉音,一跃而起,用两个前爪和头,一下子捕住了滚球,然后用鼻子推着球,边哼着,边把球推向客厅。 待狆狗抬起头,等待主人夸奖时,晓坤加上一脚,那球再次向阳台飞去。狆狗看见突然飞走的足球,稍稍迟疑了一下,不想晓坤怀中的“骚哥”,这时腾身而下,向着阳台方向猛扑而去。 看看“骚哥”就要用翅膀抱住飞旋的球了,可是,转眼间,由于球的速度实在太快,不等“骚哥”将球夹稳,那球竟一下子将“骚哥”冲翻在地,从它身上跳了过去。 “哼,这球竟然也不给面子!”“骚哥”咯咯着,张着两喙,一翻而起,又跳到将要停止滚动的球顶上,用那又硬又尖的嘴,对球狠命地啄了几下,算是报了球不给面子的一跳之仇。 (二十八) 看着“骚哥”扑球骄健的身姿,我们大家乐得鼓起掌来。也许是刺猬眼红“骚哥”,也许是害怕足球代替刺球吧,总之,就在“骚哥”站在球顶搔首弄姿时,那只不见身影的刺猬,又突然窜了出来,它用身上的长刺,把足球猛刺了一阵,然后,又像雾团一般,在室内滚了几滚,就窜进卧室失踪了。 那只站在球上玩味的“骚哥”,那时只顾得意,哪里防着,一下子竟从球上栽下来,摔了个大跟头,把一点底子给掉光了。 卧室里,熟睡的小外孙,正翘着光屁股甜甜地沉睡着。为了防止刺猬的搅挠,我和晓坤把卧室找了个遍,没有发现它的踪影,于是,我们只有保持不动,以观动静。约有抽一只烟的功夫,卧室床角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声音,循着那个方向,我们好像影影绰绰看见一个灰灰的东西在蠕动,因卧室光线太暗,视觉不堪分明。我急忙打开电灯,一看,呀,好个聪明的坏蛋,原来正是那只刺猬,它此时利用墙和床脚的间隙,将身上的刺一张一收,已爬上了床,几步窜到正在熟睡的小外孙身边,眼睛瞄着他胖乎乎的屁股盘,正在那里龇牙咧嘴呢。 我的个妈呀,这可不是好玩的!刺猬是个杂食的动物,它见到肥肥的屁股,可不会轻易放过的呀!我想,它说不定会试着,用它那长刺,把肥肥屁股蜇起,背到背上,再搬到洞里去享用呢。当然,刺猬背是背不动的,但这个鬼主意却十分可怕呀。 我正猜着,那只不要脸的刺猬,鼻子在小外孙的屁股旁嗅了嗅,接着就后退了两步,背部凸起,向上高高竖起长刺,它真的想把屁股背走?我倒抽了一口气,气不打一处出,冷不防抓起一只皮鞋,朝刺猬狠狠打去。 刺猬见状,大惊,它慌不择路,从床上飞跑至床沿,像一个球,滚跌下床,在几声叭嗒叭嗒的脚步声后,没了踪影,我和晓坤找了找,没找着,只好暂时作罢。 (二十九) 我们大家决定到汉阳龟山郊游去,为了路上方便,我们准备了两根绳子,一根套在狆狗的脖子上,由偲偲牵着,一根系在“骚哥”的腿上,由晓坤带它。临出门,“骚哥”烦躁不安,又扑双翅,又啄脚绳,牵它走,它也不动。我们见此情况,就替它解开了脚绳,并作好了思想准备,万一路上“骚哥”走失,就只当是放生了一只家禽的。 出门后,偲偲牵着狆狗走在前,晓坤抱着“骚哥”跟在后,那“骚哥”紧贴着晓坤的肚子,抖动着红冠子,似乎在为去掉脚绳而得意,一路上,它不停地转动着眼珠,看看街上的行人,瞧瞧疾驶而去的汽车,时而把一条腿伸出来,时而又缩回去,但不管怎么动,它总有一只爪子,紧紧勾住了晓坤的裤腰带。就这样,我们大家从位于汉口香港路的我家,乘上专线车,再渡过汉水,就来到了位于汉阳的龟山。 春日的龟山,满山清翠,郁郁葱葱,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上山石径,一步步地往上爬,在路上,乘车坐船时,这狆狗和“骚哥”也还算听话,与我们片刻不离。到了龟山后,那只狆狗神气起来,它兴高彩烈,头也不回,一直住山上跑,边跑还边追逐山上的野鸟。但那只“骚哥”却不然,它像个犟头螺丝,大张着两腿,就是不肯走,怎么哄,也哄不动。晓坤见状,忙对我说:“舅舅,搞犟了,我们先走,看它么办?” “骚哥”在打什么主意?我们几个在登山途中都在猜着。“你的档案中有没有记载?”我问晓坤。“有的,它好像是想等会露手。”晓坤思索了一会儿答道。 我们爬到离“骚哥”有近五十米远的高处时,从山上往下回看,那“骚哥”仍站在原地,已像一个小不点的鸡娃了。“他会不会丢?”我正在疑惑,晓坤突然抬起手,拍了几下巴掌,口里吹了一声哨,嗨!直乐得我们大家喜上眉梢。只见这只“骚哥”灵犀一动,腾飞而起,它向上山的石径方向纵了纵,不几下子,就飞到了晓坤的身边了。 “啊,这就是‘露手’!”我们几个大悟。休息时,“骚哥”就在我们周围玩着,也不走远,它时不时地叫唤几声,啄啄草,抓抓土,抖着翅膀跳一跳,不知何时,它居然在草丛中逮到了一个胖胖的大蚱蜢。它咬着这个大蚱蜢,左一撞,右一摔,将蚱蜢弄晕了,然后,就把蚱猛丢在地上,像忘记了似的,走开了,顺便从地上又叼起一片树叶子,“咯咯咯”地叫了起来。 我们又继续登山了,待我们再回头时,我们与“骚哥”的距离,大约也有百公尺远近,看看那遥远的“骚哥”,它仍在那儿玩着,并时不时地瞧瞧我们登山的方向。过了一会儿,晓坤把手举了起来,开始向它摇动,那“骚哥”一见这个动作,就迅速飞腾而起,翅膀一路煽动,双爪三不知在山石上点动一下,连飞带跑,很快,它就落在了晓坤的脚下。接着,晓坤“嗖嗖嗖”地爬上了一棵树顶,“骚哥”就“嘟嘟嘟”地绕着树跳,它那嘴上,竟还叼着那只大蚱蜢呢! 时间一长,“骚哥”跳着跳着就打了野,竟跳到离树较远的一堆灌木旁,晓坤乘机下了树,躲在一个岩石后面,我们也全都藏了起来。 “骚哥”站在灌木旁,把蚱蜢叼起,抛向空中,又从空中,准确地接在口里,抛着、接着,“骚哥”忽然向上一望,“乖乖,晓坤怎么不见了?”它“咯”地大叫一声,扔掉蚱蜢,像丢了魂似的,“咯咯咯”地飞上树顶,慌慌张张四处乱瞧,忽地又冲进草丛,东奔西窜,“咯——咯——”地拉长声调,悲鸣着。 我们见状,就从岩石后面放出狆狗做引线。那狆狗快乐无比地跑了过去,冲着“骚哥”一扑,然后返身就跑。“骚哥”一发现狆狗,神情立即镇定下来,它紧紧跟着狆狗,一刻也不放松,一直到岩石后面,看见晓坤,就飞扑到他的怀中,把胸袋贴着他的胸口,撒起娇来了。 愉快的郊游,让这家禽们快乐无比,我们一家自不用说,回家时,狆狗步履轻快,屁股两边甩动,一到大楼单元门栋家门口,狆狗就挣脱了牵绳,飞快地跑上七楼,站直身子,扒在我家门上,用两个爪子对着门又擂又抓。“骚哥”则紧跟其后,昂首阔步,走过几个楼梯转折平路,一层层楼往上飞跃,到了我家门口,它也一个劲地啄门,并用爪抓门。就这样,因多次出游,天长月久,我家那可怜的门上,竟麻麻点点的,中间杂似弯弯曲曲的深槽,那就是这两个“坏蛋”留下的杰作。 (三十) 太阳快要下山了,一轮残月挂在树梢上,照着整个阳台,使阳台呈现出一片血红色,那鹦鹉看见跑前跑后,快乐而归的鸡狗,有几分妒嫉,也有几分酸楚,它们涌向笼子边缘,抓住笼格,脑袋对着鸡狗点着,喧嚷起来。我仔细聆听着,不知怎地,心潮竟也随之而翻腾起来。细细地一辨,那喧嚷声,不尽相同,我想,那其中不同的音调,不正是鹦鹉在抒发着丰富的情感吗? 辩着鹦声,使我和家人油然而升腾起田园的乐感,那乐感非常地动人,撩发出我们的百般感受来。 “啾嘶——啾嘶——”这是抓住笼格而摇晃的雌鹦鹉声,那鸣声,“啾”音短暂,带有不平调,“嘶”音拖得较长,颇有凄凉感,那好似在哀怨着:不自由,“毋宁死——毋宁死——”这哀怨,使人联想到了贝多芬和他的命运交响曲,眼前的鹦鹉,是在艳羡鸡狗的得意、自在,还是在以短调当哭,哀叹自己笼中的命运呢?那只有由着你去猜度了。 “啾、啾、啾!”那是一只边叫边扭头而鸣的雄鹦鹉歌调,那调音轻柔而有弹力,有揶揄的味道,也有温馨的感觉,它很有一点孟德尔逊与舒伯特乐曲的清韵。那分明是鹦鹉在妒嫉地嘲笑:一次效游,就乐得忘形的“轻生骨头”(轻浮)的鸡狗,“羞!羞!羞!” 快乐了一天的阳台,终于静了下来,禽鸟们也疲了,歌声中止,阳台上的居民们全都静静地歇息了。 “茹晰——茹晰——”不知何时,一声声凄绝哀婉的鸣声,打破了这宁静的夜,把我从沉睡中唤醒。听那声音,好像来自阳台,我赶忙披衣起身,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循声张望。那亮窗处,夜色蒙蒙,路灯和远处高楼的灯光散映在阳台上,我估摩着那时辰,可能已到五更了。在微光下,我发现了一只站在我家阳台弦外玫瑰花丛中的杜鹃。 深夜里,这杜鹃不知何故,在那里哀哀地啼着,它那模糊的身影和玫瑰花的阴影重叠着,给阳台“音乐”的“乐”音,渗进了几分历史的幽伤,它是在那里向阳台的禽鸟们报告暴雨的将临,还是在追忆着那泣血的往事? 我早年逝去的父亲曾告诉我,杜鹃的啼声,是一种声籁,它是蜀国的望帝死后,幽灵所化,每到春季,杜鹃就会回来,杜鹃鸟叫了,那亲人飘游的灵魂就要回家。白日阳台上的融融之乐,是否引来了我久逝的亲人?如有,那又是谁?是父亲,是母亲,是两个姐姐和大哥?我这样地想着,这样地盼着,耳畔不禁响起了我大哥金如遗留笔记中所写的一首《杜鹃啼血》诗来: 静夜,那东方飞来一只杜鹃/悄悄地在玫瑰旁歌唱/惊吵了那宁静的夜/那可怜的杜鹃啊/嘴里已经唱出鲜血来了/人们谓之为杜鹃啼血/然而,那美丽的玫瑰啊/知道吗/这又是为谁在歌唱? “为谁在歌唱?”面对着眼前的杜鹃,我思索着,追忆着,猜想着。天,更黑了;电,闪了;雷,响了,暴雨倾盆而下,那只杜鹃,在暴雨中,仍在凄厉地哀歌着。突然,从楼梯上,由远而近,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我的心,紧张起来,难道这杜鹃的哀声,真的为我呼唤来了那逝去亲人的灵魂? “咚咚咚!”门口果然响起了敲门声,我的心竟也“咚咚咚”地跳起来:是清晨的幻觉,还是灵魂的降临?“咚咚咚!”那敲门声越来越响了。我摸摸门,门有颤动感,还真的来了!我的心狂跳不以,不知是惊,还是喜。“刘锋!刘锋!”那门外传来急促的喊声,我听听,有点耳熟,就打开门外走道的电灯,贴着房里门上的“猫眼”,偷偷朝外一看,啊,门外既没有亲人,也没有灵魂,而是三楼的领居老徐来了。 我赶紧打开门,只见老徐提着一只深筒套鞋递了过来,生气地对我喊着道:“你看,你家的刺猬害不害人,它夜半三更跑到我家捣蛋,竟摸到我媳妇床上,把我媳妇的屁股锥得血流。我听到房里的惨叫,还以为媳妇的房里出了流氓,等我拿棍子冲进去打时,随么事都冇看到,我们搜索了半天,才发现是这个鬼东西,它竟钻进了套鞋,倒又倒不出来,真是个狗东西,流氓!”说完,他把套鞋丢在了地上。 “怎么惹这大的祸啦?”我赶忙一个劲地向老徐赔不是。望着悻悻而去的老徐,我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亲人的灵魂没见着,倒引来了灾祸;笑的是,这不要脸的刺猬,总是把人家的屁股当肥肉或面包、西瓜什么地背,还害得狗又挨了顿骂。 (三十一) 天,好似已经透出了一点白光,雨,停了下来,我把老徐家的套鞋放到阳台上,等刺猬自己出来。刺猬,不“扫黄”,不到夜半,是不会轻易出来的,那就只有由着它了。而那只可怜的杜鹃啊,此时,它仍在玫瑰旁一声声地啼着。借着路旁的一丝亮光,我定了定眼神,终于看到了杜鹃嘴角鲜红的血色,唉,在这无限快乐和百感交集的阳台上,趁着这即将开始又一个新的黎明,我将无限的情怀寄于:乐感飘飞的自然天籁。 《阳台趣——花木宠物系列感悟》下一节:《憨狗的百趣》 以上图片均来自于网络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dingchong.com/djhyf/1439.html
- 上一篇文章: 陈宪一讲定位风波和爱情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