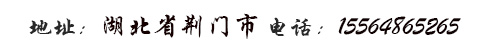舟山潮水山水舟山
|
治疗白癜风有什么好办法 http://m.39.net/pf/a_5818755.html 山水舟山 文︱舟山潮水(一) 舟山是我的家乡。舟如山,山如舟,是谓舟山。这个地名取得形象而贴切。据说康熙皇帝是不喜欢“舟山”这个名字的,“以山名为舟,则动而不静”,诏改舟山为定海山,把已经有的定海改为镇海。舟是动态的,虽是固定的山之舟,皇帝也害怕忽然拔锚远离,要把它围住、定住,叫定海,可说是颇费苦心了。历史上的舟山从来没有离开过大陆,不像台湾,也不像香港。它忠实地泊在浩瀚东海,既倾听着大陆的声音,又把眼光不时地投向太平洋远处。我有时候很奇怪,怎么大陆的各种流行,从政治到文化乃至服饰,虽然慢了半拍,最终都要在舟山风行一番;也吃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很早就漂泊到北美、南洋,以至现在舟山也算得上是个侨乡了。转念一想,都因舟如山、山如舟的缘故。它是山,所以它不动;它是舟,所以它又动。 (二) 舟山的山,和大陆的山比较,实在是说不上是山的。先天性的毛病是,外观并不高大、雄伟、险峻,内在的又没有多少矿藏。但是,舟山的山也有自己的特别之处。老家屋后的山叫火龙岗。小时候想看海,不出几分钟就可爬上山顶了。清风吹来,俯视远处,海上白帆隐隐约约。定海港对面的五奎山,看上去真像只蠢蠢欲动的小乌龟了。登山观海,在舟山是件稀松平常的事。登高山、名山爬得气喘吁吁,耳听的声音,只能叫做松涛,眼看的云雾,只能叫做云海,实在是体会不出海有多么神秘、多么无限,又多么蔚蓝、多么浩荡的。大陆的山是仰之弥高,你面对的是位威严的长者、慈祥的老者;舟山的山是俯之更近,你面对的是位谦恭的学徒、散淡的友人。大陆的山,你要亲近它、感悟它,要做许多庄重而心跳的准备,而舟山的山,你像串邻居的门那么方便和温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舟山的不少山,特别是在没有像样平地的岛山上.密密麻麻嵌着一排一排的石屋,多少年多少代,人们在山上爬上爬下,而不感到山的呼吸有多沉重。出海打鱼归来,船靠上山,人就感到一种充实、一种解脱、一种安逸、一种幸福。山之高低,山之大小,山之好坏,一概是不计较的。 在我的观念里,舟山的山是绝对没有高山、大山的气韵和格调的。 但是,去了黄杨尖山,这个观念有所动摇。那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后,我们几个乘着一辆吉普车缓慢地爬进了山里。起初的味道和上众多的无名小山一样平淡无奇,逐渐地外界嘈杂的人影禽声消失了,色彩斑斓的树林密密麻麻地压过来,公路下的流水伴着潺潺的声音忽隐忽现。一股弥漫着沉默是金的气息如同雾般逐渐浓烈起来,看不见山顶,看不见海,看不清四周。我感到了黄杨尖山的落寞。所谓高山、大山都有这种无法言说的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地压迫你的落寞。如同养在深闺无人识的落寞。这样想着,车却停了下来,原来桥坏了。车熄了火,万籁更寂。在我的鼓动下,我们几个爬得气喘吁吁,终于登上山顶。山顶白云飞扬,风声吹彻,杂树丛生,野花摇曳。极目远处,海天辽阔,正是晴好日子,岛屿沉浮,如舟行,如花开,如星坠。据野史一鳞半爪记载,黄杨尖是葛仙翁炼丹之处,悠久得和四川青城山的道教圣地可以媲美,但最终未有道教的点点滴滴遗迹可以寻觅。如今的山顶亦佛亦道,大抵是些民间粗俗的小宫小庙之类的东西,似乎想复活过去遥远的记忆,然而功利性的求神拜佛活动,使这些简陋的建筑物根本无法折射出道教本身内在的对生命终极的感悟,以至显得不伦不类。黄杨尖山终究没有留住葛仙翁,也许风太大、树太小、泉太细……也许葛仙翁压根儿没有来过,一切不过是人们的杜撰。 如果说黄杨尖有高山的崇高气,那么摩星山则有名山的空灵气。 岱山,人称蓬莱仙境,我理解大抵是因为有摩星山的缘故。那是一个春雨潇潇的季节,我有幸住在摩星山招待所。站在走廊,俯瞰山下,细绵的雨丝在起伏的隐隐约约青山中、大海上浮动,如同无数琴弦委婉轻挪。一会儿,雨过天晴,海上沉浮的一个个岛屿撩开轻纱,好像是醒来的鸟睁开透明的眸子。这种景象也许你在古代的山水画、山水诗中见过,但翻遍历代画作、诗卷,没有任何文人为之歌之、吟之。据传宋朝大文豪苏轼过兰山、秀山,留下了“兰山摇荡秀山舞”的佳句。不知何故,苏轼没有登上摩星山,这或许是摩星山永远不能抹去的隐痛,但岱山人却一直不肯错过这座空灵之山。也许摩星山的寺院有那么一丝土气.缺乏那么一种庄重;也许碑刻着的本地作者的书法并非是大家名家;也许摩星山下的诗人至今仍是默默一群;也许清墩的游戏不足与外人道,但谁能怀疑时间不会把摩星山造就成真正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名山呢? 在舟山众多有名或无名的山中,我最喜欢的一座小山偷偷地躲在远离本岛的泗礁岛上。它就是大悲山。舟山的山,用佛语作为地名,给我印象深的,除普陀山、洛迦山之外,一个是观音山,另一个就是大悲山。大悲山是冷寂的,很少有人去大悲山寻找心理对应;大悲山又是简陋的,没有普陀山那种金碧辉煌、连绵不绝的寺院建筑物;大悲山更是肃穆的,除了松树,就是一些渔民出海遇难的新旧不一的坟墓。初听到这座山的称谓,我的心为之一颤。普陀山、大悲山遥相对应,而大悲山蕴含的更加具有超越世俗一切,进而上升到“形而上”的意义。与其说是一座山,不如说是阐述生命哲学的一个景象。我原先理解大悲之说,是和渔民们长期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搏斗生存需要寻找寄托有关。人生悲怆,生命悲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生命之船拔锚开航就永无回头之日,这才是人之大悲,生之大悲。然而查了佛教书籍才知并非如此,大悲和大慈相连,那是对悲怆境遇的悲悯,是人类对自己苦难更深层次上的抽象审查,从审美意义上讲,这种审查更加理性,更加超然。荣辱、是非、得失,大悲之下,如此渺小。我无意拔高嵊泗渔民的精神境界,但在遥远偏僻的边岛上出现大悲山,实在是对舟山人精神生活的呵护和关怀。 非常遗憾的是上述这些山,到如今名声都不大。“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话当然可以这么说,但不是高山、大山,“仙”们恐怕是不肯去或呆不长的。当然。普陀山无论如何是个例外。论山势,它和那些巍峨、雄壮、险峻的大山、名山实在无法相比,但是它秀气、含蓄、和善,就像那位洒着杨枝水的观音那样。如果说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是肩负着至尊至大的阳刚之碑,那么普陀山则低眉顺眼地扮演着一首绝句、一棵莲花、一个盆景的角色。但是你实在无法小看它,你不知道它把自己藏得多深、多玄,终日传出几声佛鼓、几缕涛声。而把根子把真实把至尊至大都藏到无边的海水之中了。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在百步沙的一个亭子里,我与一个小沙弥讨论普陀山香火越来越旺的缘故。小沙弥抬头望了望黑沉沉的海面,不假思索地说,水养的。 (三) 舟山的水若论淡水,和内地的江河湖泊是无法比的,贫乏得连一条有名字的河流都没有。但是要论海水,那就令所有的淡水失色了。海纳百川,什么样的淡水能有那样一种吞吐四方的胸襟,那样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度,那样一种至柔至坚的力量,那样一种生生不息的循环,那样一种周而复始的潮起潮落,铸就了多少“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亘古不变又常看常新的景象。 初来舟山的外地客都遗憾舟山的水太浑,他们习惯于书本上说的“蔚蓝的大海”等描述。从审美的意义上说,浑水确实给人一种不舒服感,然而舟山之所以有名,却和这浑水密不可分。水至清则无鱼。正是敞开胸怀迎接了陆地上江河之水,才造就了饵料丰富、名闻遐迩的舟山渔场,才使得舟山的鱼特别鲜美。 其实,舟山的水也有蔚蓝清澈的时候。一入夏,台湾暖流裹着大块大块的蔚蓝色浩浩荡荡地涌杀过来,浑水就被深深地埋在海底了。这时候的海水会把你的眼神都染得碧蓝透明。如果你有机会坐飞机从高空俯瞰下来,浅蓝色的海水和深蓝色的海水有如麻花绞在一起,也像两条不同颜色的飞龙舞在一块。在阳光的照耀下,整个海面跳跃着金色的花斑。如果你坐船远离本岛,驶向茫茫的大海深处,那你更有机会看到那种刺骨惊心的蓝水。 海水之蓝,来自于它的广大无比。你越看到深蓝的海水、你越看不到海水的尽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就为了看到那真正的海水,我坐一天的船到花鸟岛,复坐一条小机帆船,漫无边际地向大海深处驶去。开始海水是湛蓝色的,透明得看得见清水滩的礁石和绿色的藻类,慢慢地海水变得有些乌蓝,除了一两只海鸥从船头掠过,什么都没有。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海水变得浓稠起来,宛若原油似的,大块大块闪动着烤蓝色的光芒,一波一波富有质感地涌来。这时,船熄了火。四周是拱着龙鳞似的涌浪,海天相交处是一片灰蒙蒙的光团。那种在高山、大山深处才能感受到的渺小和寂寞不可阻挡地从我内心深处升起。我把手伸向海水,仿佛是在伸向遥远的过去,又像在伸向不可企及的未来。时间在这里停止,空间在这里凝固。 如果说内陆的水,组成的是江河湖泊,就像人的血管,是维系生命的通道,则舟山的水,组成的是大海,就像母亲的羊水,是孕育生命的摇篮;如果说内陆的水是风景的点缀,则舟山的水是存在的本身;如果说内陆的水是山养的、地养的、人养的,则舟山的水养着岛、养着山、也养着人。水是路,舟是车。道路有形,水路无形,有多少水,就有多少路。舟山的水载着舟把人送向远方,送到世界的角角落落,也许回来,也许永不回来,也许带回生存,带回快乐,带回幸福,也许什么都带不回,连自己都不带回 舟山的水不仅是舟山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水,也是养成舟山人审美品位的精神之水。舟山人游了长江三峡后,大都觉得不过尔尔,全无外地人的兴奋和激动。有一次,我随舟山几位老乡同漂长江三峡。看了瞿塘峡后,他们几位就不再看巫峡、西陵峡了,躲进客舱又热火朝天地打起“清墩”来。外人诧异,花这么多钱,不看风景却去打牌。答曰:“在舟山不少岛周围,上船随便绕上一圈,水都比这里清,比这里急,比这里广。”我一开始有些不以为然,但到过岱山县的叮嘴门水道后,觉得他们也并非夸大其词。 那天,我们几个的本意是去看叮嘴门网箱基地的。船在长涂港,感觉就像在一条普通的河流中行驶。一出港口,海水就变得清澈起来,由小岛对峙而形成的“门”(实际上就是峡)一而再、再而三地冒了出来。海水卷起一堆堆飞雪,冲刷在两边的岩石上。岩石的形态奇形怪状,有的沟壑纵横,犹如人的皱纹;有的光洁滑溜,宛若栩栩如生的动物。让人不得不惊叹海水之刀在时间女神的帮助下,把岩石雕刻得如此苍老。虽然叮嘴门两岸没有三峡两旁积淀的历史文化遗迹,但不时掠过的被海水鬼斧神工般修理过的沉积岩礁丛,同样让人感到时间的流逝、历史的悠久和人生的永恒。 我一直认为,所谓遗迹,重要的在于启示和感悟,至于是一汪水、一块石还是一间屋、一座墓那是次要的。最让人心动的是,倒映在海水里的茂密森林。在人们的感觉中,湖中的树木倒映是美丽的。没有想到在汹涌海水里倒映着的森林,竟能把柔美和刚烈结合得如此完美。我至今还难以忘怀的是那倒映在海水里的一丛杜鹃花,红花蓝水,似动非动,欲静非静,让人如入梦月一般。在舟山众多类似的港湾、峡门中,这样的景象并非少数,如能开发出来,供外地游客游玩,他们该是能获得一种崭新的体验的。 大多数日子,舟山的水是欢快,是处女,是春风,是随和,馈赠一切;而也有些日子则是阴沉,是咆哮,是虎狼,是战争,毁灭一切。年轻时候读书,关于水的力量的描述,印象最深刻的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和“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而,经历了年的那次台风,我感到古人描写的不过是江湖的杯水风波。那天,我站在定海区大沙乡的一条海塘附近,目睹了海水从微啸到狂叫的整个过程。起初海水只能在塘脚下拍出无数根水柱,在凌空开出惨白的焰火后,整个海面都怪叫起来,升腾起一群群雪豹,争先恐后地踢破海塘,海塘后面的芦苇纷纷倒下,挣扎着想从水中冒出来。那次台风后,我跟随市受灾慰问组来到嵊泗县的嵊山镇,亲眼目睹沙滩边的公路被海水炸得东一坑西一洞,两层楼的冷库一层已被削到远处,仿佛被导弹轰炸过似的。海滩上漂粘着被打成碎片的船板,凄厉的哭泣在新坟旁响起。 然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即使风和日丽的曰子里,舟山的水也用那种平静、谦和、温顺的神情,包围着你,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着山,捆着岛,也拥着人。让你想动动不了,想走走不了。看上去水路无限,其实无路可走;只能困守在岛上、山上,困守在孤独的一隅。内陆发洪水最广最长,也有消退的一天,而海水却是捆着你直至天荒地老,让天地也慢慢地变得只和岛一样宽、一样大…… (四) 在舟山,所谓文化,从某种意义讲,不仅仅是海洋文化,而是岛与舟的文化、山与水的文化。山使人宁静自守,敦厚纯朴,而水使人开通,与时俱进;山使人叶落归根,而水使人闯荡四海;山使人觉悟人生的永恒如日月永恒,而水使人领受人生的流逝如昼夜不舍。这些都是从正面来说的。倘若从负面分析,山使人封闭保守,坐井观天,水使人随波逐流,缺乏定力;山使人知足常乐,怡然自得,而水使人浮躁不安,急功近利;山使人感到生命的渺小,而水使人感到世事的无常。 这样说,并非是要描述舟山人心里的“集体无意识”,也决非是概括舟山人的文化特质。我们徜徉在山水之间,我们的存在自然会烙上山水的印记。外地人常常搞不清舟山人吃月饼比内陆慢一天,但月饼不是不吃;看上去比较闭塞,但很早有闯荡南洋的;似乎惯于安逸,但却一口风一口浪,和海龙王争食;常常少见多怪,但各方面的眼光却不逊色于大城市。其实,山水舟山不但是我们的物质家园,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如此就能理解我们自身存在的常常是“二律背反”的性格和行为。 至于山之优劣、水之是非,作为舟山人,我最喜欢明代都督侯继高在枸杞山督汛题的四个字:“山海奇观”。 欢迎转发 请点在看 本号原创,如欲转载请后台联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juanhuaa.com/djhxj/5318.html
- 上一篇文章: 金根琴花骨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