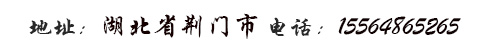有冰川擦痕的人百家故事人物
|
本篇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目#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冰雪夺去了崔之久眼睛的健康、右手的五根手指和同伴的生命,但这并没有使他离开,反而让他一生的命运正式和冰川相连。 文|张炜铖 编辑|姚璐 摄影|尹夕远 有限 在起伏的地球表面,有一条隐形的线,海拔在此之上的地方即是积雪终年覆盖的世界。它具有强烈的边界意味——不再消融的雪可以形成冰川,大多数人类活动在此终结。冰川学家崔之久的研究以此为起点向上展开。 在冰川发育典型的青藏高原,雪线高度可以达到六千米。这表示他需要不断抵达那些高地,即使这带来巨大的危险。他是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进行地貌研究的学者,在自年起从事这项研究的最初几年里,冰雪夺去了他眼睛的健康、右手的五根手指和同伴的生命。但这并没有使他离开,反而让他一生的命运正式和冰川相连。 但在88岁的这一年里,崔之久觉得自己将要和冰川告别。他去了一趟玉龙雪山,这座山的冰川曾经在年发生过一次高速崩塌,当时他恰好在丽江,亲自去勘察了现场。17年过去,他再度前往这里,想观察它的变化。困难显现了,在本该如履平地的海拔多米高度,他发现自己走不动路,腿脚不听使唤。一个一米多高的坎出现在眼前,他爬不上去,只能先坐在坎上,再慢慢把脚挪上去,最后站起来。 在三四年前,他的感觉还不是这样,在野外,走上几公里不成问题。而根据他的学生、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威回忆,年左右,崔之久完全可以跟得上年轻的学生们,兴致高的时候还会唱李娜的《青藏高原》。衰老的气息拖延了很久,终于还是找上门来。 和很多守在书斋或实验室里的学科不同,地貌学要求研究者进行大量的野外实地考察。在野外的力不从心意味着在科研里的某种退场。在这个行当里,跑野外最多的老先生也是干到88岁,崔之久算是平了这个纪录。而人的生命长度,在冰川的纪年面前不值一提。 晚年开启的生命中最后一个课题让他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冰川如何形成的宏大命题。中国的冰川和南北极不同,属于中低纬度冰川,与高山拥有很密切的关系,它的出现是气候变化和地质构造运动耦合的过程。做区域的冰川研究,冰川学家们已经很熟练,而这样宏观的课题在当今的研究中并不多见。崔之久希望他的研究最后能归结于这里。 年年底,他开始着手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9月,《青藏高原第四纪冰期旋回与构造隆升耦合机制及过程研究》项目批准书下达,次年1月,正式开始执行。北京、兰州、广州等地的研究者们都被调动起来,张威也作为合作者参与其中。在他看来,只要是研究冰川的人,看到这个课题都理应兴奋。项目的研究重点是青藏高原东缘的数十座林立的山头,为了调查冰川地貌和沉积物的分布特点,各个单位加在一起,出了20多趟野外。 问题出在如何测量这些冰川的年代上。过去,学者们都是用地貌的相对年代来描述冰川形成的时间,但是这一次,崔之久需要更准确的绝对数据。学界流行并认可的两种测年方法,光释光测年和宇宙成因核素测年,在冰川面前都显得非常无力,它们只能提供最多10万年级别的精确结果,而现在留存的第四纪冰川要追溯到一两百万年前。方法上的无解让所有兴奋的情绪到此为止了。年,整整做了5年的课题落幕,在崔之久的评价里,收尾收得不是很好。 课题是我最想做的,所以用它收场了,我也很高兴,但是这个结果我并不高兴。崔之久面对着一个不太完满的结果,但他相信,只要能够经受得住等待,沿着他未竟的路途,这个问题总有被解决的一天。学生张威是他最信任的继承者,事实证明,在最近的几年里,张威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认识到自己的限度并没有让崔之久过分地沮丧:如果是我自个儿没做到,我可能要后悔一辈子,但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有一点遗憾,不是很强烈。面对冰川,他从来都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即使是在登山科考的过程里,他也没有那种强大的征服高山的欲望。有一种更稳定的情感支撑着他的工作,那是经历过人生里的重大事件之后存留下来的信念。 夺走 崔之久希望自己能和冰川有个正式的告别,它应该发生在贡嘎山海拔米的一座纪念墓碑处。被纪念的人是年攀登贡嘎山时的四位牺牲者丁行友、师秀、国德存、彭仲穆。 年初夏,登山队19个人从康定骑马出发,中途翻越海拔米的子梅山,历经7天,到达贡嘎山半山腰的贡嘎寺准备攀登。这是一段极其美丽的旅途,沿途青冈林和杜鹃花交错,构成一幅斑斓的景象。而贡嘎山呈完美金字塔形的主峰,与他们遥遥相望。海拔米的贡嘎山,因为交通较为方便而被选中成为此行的目标。更宏大的背景是,年,中国登山队组建,中国的登山运动正式开始。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由全国总工会从各地的工厂抽调而来。当时的体委主任贺龙指示:登山要为科考服务,以扩大和延伸登山的社会效应。三名科学研究者被选中一同参与登山,北京大学地理系研究生崔之久的任务是对贡嘎山的冰川进行地貌考察。在此之前,崔之久进行的是经典的黄河地貌研究,冰川是他从未涉足的领域。临行前,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打电话把他叫到中关村的办公室,与他谈话,告诉他冰川是大自然的温度计,他才知道冰川研究的意义。 年能够登顶,与其说是一次胜利,倒不如说是一个奇迹。登山队另一位成员刘连满只要回忆起这次攀登,就会陷入长久的沉默。贡嘎山虽然海拔不高,但是以峰顶为中心,半径10公里之内的山体高差达到米,这是十分罕见的起伏。横断山区的条冰川汇聚在这里,平静的冰雪之下,隐藏着断裂、缝隙和雪崩的隐患,但初尝高海拔登山的队员们对此甚是懵懂。 雪崩是在海拔约米处发生的。当时他们正从米的陡崖下部向上部多米的骆驼背攀登。在横过一个狭窄的雪冰槽时,崔之久听到前面有人喊,雪崩!他抬头一看,看不清体量的雪从他的左侧滚落下来。他还来不及退后,就被雪抛起来,在空中下坠。 被翻腾的雪崩潮包裹着,他没有任何痛感,只感觉自己轻飘飘地在飞。他的神智很清醒,甚至很清晰地闪过了这下我完了的念头。雪崩的速度是每秒30米,十几秒后,他从空中落下,发现自己被卡在一个冰洞的中部,头朝上,脚在下,身体被深深埋住不能动弹。残留的雪不断落下,打在他的脸上,他侧过身去,拼命扒开头部的雪,让自己能够呼吸。直到雪崩停止,他的头部还留在外面,他还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研究者一起结组,前面是组长,后面是同样来自北京大学、此行负责气象观察的丁行友。雪崩停止之后,他拉前面的结组绳,救出了被埋在雪里的组长,但是后面的结组绳已经断开——想象这股巨大的力量,结组绳可以承受公斤的拉力。等到他们找到老丁,把他挖出来时,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这一幕在崔之久心里永远挥之不去。这之后,还有三名队员,因为从悬崖上滑坠而死。哪怕在暮年,拥有了那么多和冰川有关的回忆,最常让他想起的,还是这次山难。 当时中国没有人研究冰川,崔之久只能找到一本苏联翻译过来的《现代冰川考察手册》,照着上面的方法进行测量。年,他把此行收集的科学资料写成了论文《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刊发在《地理学报》上。这篇论文中记录了冰川事业的残酷:事实证明,只有在米的山脊或者更高的地方,始能比较全面地看到贡嘎山现代冰川的面貌。 年,中国登山队组织攀登祁连山;年攀登慕士塔格峰,崔之久都作为科考队员随行。令他自己也感到费解的是,决定继续攀登的时候,他脑子里并没有阴影或恐惧,脑子里没有害怕,因为我只要有一点害怕我就可以不干,我的导师不会说不行。 在慕士塔格峰,他依照自己所做的详细的科考计划,研究雪线之上的地貌和冰川。为了照相和做笔记,他需要不时地把手套脱下来,反复之中,到米的时候,手已经麻木了。当时没有专业的宽边雪镜,米的时候,因为光线从眼镜的边缘不断射进来,他出现了雪盲的症状。那时他的手没有知觉,加上看不见东西,他还以为自己戴着手套。到了营地,他的手已经不能动了。 他把手包起来,由同伴扶下了山,先是骑牦牛到喀什,然后经历转机,三天后回到北京。医院,把包裹着的布打开一看,发现手指已经变黑。 崔之久回忆说,我本来希望他从中间截,我还可以多留一点,结果等打开一看,我什么话也不说了,没有可说的。几乎连根给你拔了。做手术是局麻,他躺在床上,可以听到医生剁掉自己手指的声音。由于雪盲留下的后遗症,他的眼睛很容易流泪,与《人物》对话时,他需要不断地擦拭眼睛。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是生活里的重大悲剧,但是崔之久却淡然地接受了。他还是继续用右手,用大拇指和食指残留的缝隙夹住笔和筷子。那是一种常人难以体会的、幸存者的心境:你想他们命都没了,我这算什么啊,所以我根本不当回事。我这一辈子真的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面,无所谓。跟生命相比,你这几个手指头算怎么一回事,不值一提。 擦痕图源:邮票印制局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juanhuaa.com/djhxj/11621.html
- 上一篇文章: 青岛最不能错过的自驾线路,包揽世界级山海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