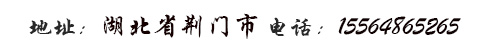独秀文学李曙生凡鸟二题
|
凡鸟二题 李曙生 一斑鸠奥义书斑鸠的踪迹布散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西伯利亚,它常常引动普里什文的猎兴。在北美洲,它成了梭罗的情人。在地中海沿岸,斑鸠被但丁比作屈服于欲望的精灵。而在古代的巴勒斯坦,斑鸠和鸽子一样被奉为圣物。汪曾祺写过一篇《伊犁闻鸠》,似乎是在意外的地方意外地听到了斑鸠的鸣声,心头油然浮起一阵莫名的快乐,实在未免有点少见多怪了。 一年四季,斑鸠的鸣声似乎只是飘拂在明媚的春季,而在春季,它的鸣声也只在晴朗的早晨才隐约可闻。斑鸠的鸣声是那么的短暂,短暂而又虚幻,正像燔祭的时候,烟云一般缭绕上升的馨香。此外,一年中的大多数日子你都听不见它待在哪里。或许它就在你居处的附近,可它却奇异地缄默着,恰像我们一类孤僻的邻居,终日深居在家没有一点动静,以此暗示外人不要去打扰他。 谛听斑鸠的鸣声的时候,我是比听别的鸟鸣声更入神的。我也常常不自觉地循着斑鸠的鸣声去寻找它的踪影,很多时候,我刚一抬眼望向那鸣声传来的地方,就看见一道闪烁的白光,宛若传说中名为吉光的神马,脚踏雷霆射入了浩荡青冥。斑鸠对我有戒备之心吗?也许它发现了我对它的好奇心,于是就像一个冷漠又敏感少女那样时时都不忘矜持地回避潜在的恋慕者?对斑鸠注意得久了,斑鸠在我心里就不可理喻地成了一种带有神秘感的特异的鸟类,虽然不论是就其鸣声说,还是它的毛羽,还有它的繁盛的种群,斑鸠其实都不过是一种极普通的飞禽罢了。就这样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对斑鸠的灵性追寻不知不觉印入了我的潜意识,成了一种动物性的神经质的反应。它让我联想到《奥义书》中写的那个梵,“它既动又不动,既遥远又邻近,既在一切之中,又在一切之外”。我无端地为它自怨自艾,甚至生出一些过后自己也感觉匪夷所思的幻想,例如把斑鸠想象成一种纯粹精神变化的实体,或者是冥冥中对我有所启示者的信使。即使我自己也知道这类幻想是可笑的,却怎么也不能把它从意识中清除。 久久注视一只铁铸般站在屋脊,映衬在蓝天白云间的斑鸠,我的思绪会随同视线一同出离我的体表,以“遥望齐州九点烟”的姿态俯视着红尘万丈奇妙变幻的人寰,这时候,虽然我的感官不能感知,我的想象力也难以理解,但我的的确确地知道,斑鸠暗紫色虹膜中间像宝石一般闪闪发光的的瞳仁透着欢笑。也许它并不是像我误解的那样疏远躲避着我,对于纷扰人类中的一个无名之辈,它保存的是亿万年前中生代时的记忆,它理应比我们人类有着更多沧海桑田的感慨。 佛家“境由心生”的论断真是一种令人醍醐灌顶的般若智慧,当我聆听别的鸟鸣声,从而生发别一类感想的时候,我更这样觉得,并不以为是自己错误的想象蒙蔽了眼睛。在江南的初夏,听着山林中小杜鹃或噪鹃的啼叫声,想着它张着血红的尖喙伸长脖子嘶鸣的样子,谁的心头不会无由地生出一种泣血的悲思呢。“一叫一回肠一断”绝非虚语,也不是夸张,杜鹃鸟的啼鸣声的确是那么的凄厉,一声声都像在倾诉着满腔的怨愤。而在清凉的夏夜,听着四声杜鹃的凄清的鸣声,我总以为它在提醒人们什么,并不是在呼朋引伴,或者照动物学家研究发现的是在求偶。而当听见布谷鸟(据说布谷鸟就是杜鹃鸟之一类)的叫声时,你的心里又会生出一种“促织鸣,懒妇惊”的紧迫感:邻家田里的秧苗都泛青了,你家的田地还荒芜着,那布谷鸟的叫声岂不正是冲着那荒田催促你吗?就不要提那种俗名猫头鹰的鸟类了,虽然在古罗马神话中它博得智慧女神密涅瓦的宠爱,被高抬成思想和理性的象征,甚至黑格尔也愿意自己像它一样,但它的怪异的鸣声却因为意味着不祥,是让人听着心里很不安的。 斑鸠的鸣声对于我却有一种奇妙的抚慰心灵的效果,那是一种另类的宁静温和的悠扬钟声。不管隔着多远的距离,斑鸠的鸣声在我听来也是那么亲切。在春天久雨新霁的清晨,东方的天际刚刚泛出紫红的曙光,斑鸠的“咕咕”声就透过窗帘传到我的耳畔。那么温柔贞静,那么富有耐心,像母亲呼唤沉睡的儿子,也像新婚的妻子看着酣睡的丈夫在喃喃自语,或抱怨哀诉。很多时候,一听到斑鸠的“咕咕”声,我就会抬眼向屋脊上寻找,偶然发现斑鸠的头顶在阳光里闪动,我就要对它报以会心的一笑。 斑鸠的鸣声似乎有点单调,但单调里依然含有耐人寻味的意义,让我猜想它是吃饱了高兴得唱起来了呢,还是纯粹因为技痒想表现一下呢,或者是为了招呼远处的伴侣呢。不知道有时候斑鸠为什么在鸣叫中突然改变了声音,甚至一边走,一边点着头鸣叫,那样子让我感到,它心里有一件很急迫的事要倾诉,它并不在乎那急迫的心情能不能被理解,只需赶快吐出来就够了。这时候我往往痴想,如果我是公冶长,也许会开导开导这只性急的斑鸠,或者相反,斑鸠对它的人类邻居有些要提醒的,就可以借着我传遍世界。 一个月光很好的春夜,我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向远处眺望,我看见对面人家的屋顶上哨兵一样站着一只斑鸠。一会儿又有两只斑鸠飞来,三只斑鸠就在屋顶上排成一排从这头走到那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这头,做着晚间的例行巡逻。显然是一致意识到守护它们眼前这片宁静月色的重大责任,它们的神态才那么的庄重、严肃。 今年春天我收到好几段外地朋友发来的视频:各地的斑鸠家族都喜添贵子,斑鸠夫妇忙上忙下地哺养雏鸠。让我吃惊的是,有一对斑鸠把巢建在了人家的窗台上,窗帘背后。从斑鸠孵蛋到雏鸠破壳,友人都用手机拍成小视频发到了朋友圈里。雏鸠的眼睛都还不能睁开,就都会张着乳黄色的尖嘴从父母的嘴里抢食了。我油然念出《诗经》中的这几句:“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我看着斑鸠父母辛勤尽职的样子,又敬佩又感动。 似乎有一种趋势,斑鸠在向城市迁徙,和人类生活越来越接近,二者越来越习惯于和平共处。我回老家的小山村去,发现山野里斑鸠很少见,它们像农村人口一样陆续转移到城市里去了。谁能说清这是进步还是一种应该引起警惕的变异?在街市上熙来攘往的迷乱中,白鹡鸰大胆地站在路边摊贩的桌子上左顾右盼,像一个好奇的异乡人,对什么都感到新鲜,要寻出个究竟。燕子把巢搭在青少年文化中心、体育馆的横梁和一些仿古建筑的斗拱上,自顾自飞进飞出,既深居在闹市,又和喧嚣的人世两不相关。尽管如此,它们也不比你的邻居更为隔膜,这些邻居往往和你同居一楼几十年,在街上偶然相遇仍然感到十分陌生。 斑鸠也是这样,它们了无形迹地融入了我们人的生活环境,天天冷眼观察我们的活动,而我们自己却陷于迷乱混沌之中。这些可爱的鸟和我们人类一同处在陵谷变迁的通道里,用彼此无法理解的眼光默默对视,仿佛惶惶地等待一个不可知的变化的来临。 二乌鸦本是吉祥鸟我的故乡,丘壑郁秀的皖南山地,在很大的区域里,近二十年都没有发现乌鸦的踪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疾伶的红嘴山雀、灰喜鹊、八哥和斑鸠,更有惯常待在河边芦苇丛中的翠鸟,却都不如乌鸦的离去那般让我遗憾。一只乌鸦(甚至是祥瑞的白乌鸦)呱呱鸣叫着,径直飞过秋收过后空旷的田野,这已成了我怀念故乡时的经典画面,多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每常回老家,在山林野地漫步,我总不自觉抬眼看瓦蓝的天际,幻想正巧遇见一只乌鸦归来,又每次都失望了。 有一年早春,在山东半岛,看见被季风吹得一律歪向南边的白杨树林中,一个个鸦巢顽强地盘踞在树杈上,一只乌鸦嘴里叼着树枝在强劲的东北风中奋力飞回它的窝巢,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我一阵兴奋,随即又让我怅惘。在更远的白云鄂博,在那么空旷、几乎有些荒凉的土地上,也看见了乌鸦的影子,却令我有些惊异了。 大前年的冬天在北京,黄昏我常常从北京师范大学一带的林荫道上走过,正逢乌鸦悄然归巢的时候,在西天渐渐暗下去的云霞映照下,我看见高大的杨树上出没着成群的乌鸦。林荫道上停放的轿车上,落满了乌鸦的白色粪便,不过幸而不曾有一滴掉在我的身上。我当时还想,这其中是不是有北漂的老家的乌鸦呢?它们似乎比故乡的农民更快地完成了城市化。 童年时站在田埂上看父亲犁田,总会有几只乌鸦飞来停在牛背上,抢吃被翻起的土块带出的蝼蛄。我对乌鸦的过于大胆常常不忿,有时就呵斥它们,父亲却对我说,随它去,随它去,它吃害虫呢。傍晚我把牛牵到河塘里让牛泡澡,又有乌鸦飞到牛身上,啄牛身上的虫子吃,这时我就和牛一同快乐了。 母亲说,在山林间劳动的时候,带上山的中饭要小心收藏好,免得乌鸦发现了。乌鸦会把饭袋的扣子解开,掏里面的玉米饼或米饭吃。母亲似乎对乌鸦的聪明比较赞许,并不气恼它们偷嘴。动物学家研究发现,乌鸦是人类以外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其智力大致与家犬相当。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乌鸦竟然具有使用甚至制造工具的能力。科学家曾做过这样的测试:在一只细颈的水瓶里装了半瓶水,乌鸦的长喙可以伸进瓶中,但够不着水,然后让一只口渴的乌鸦去取水喝。乌鸦衔来几颗小石子,填进水瓶,瓶中的水位上升了,它就可以喝上水了。还做过这样一个测试:在一根立柱的下方挂着一块腊肉,系腊肉的绳子缠在柱顶上。柱顶边钉了一根短木桩,柱顶有网挡着,乌鸦不能飞下来啄肉吃。乌鸦把系肉的绳子一点点在短木桩上绞紧,腊肉慢慢上升,终于可以够着腊肉的时候,它就可以享用了。乌鸦的聪明故事令我震惊。我因而想,也许下一种被人类驯化的鸟类就是乌鸦了。 再没有一种鸟像乌鸦那样,开始被当作祥瑞受到人类尊崇,而后又失宠甚至落到被人类厌恶、忌讳的地步的了。创世纪的洪水消退的时候,作为先驱从歌斐木的方舟中飞出的第一只鸟就是乌鸦。商周时代的中国人把乌鸦看成太阳精极尽崇拜。乌鸦还博得过慈孝鸟的美名。 但在希腊神话中,乌鸦意味着欺骗。乌鸦在中国被认作不吉祥的鸟也有一千多年了。东京大相国寺里,鲁智深和三二十个泼皮吃酒正在半酣的时候,门外杨柳上的老鸹打断了他们的酒兴,惹得鲁智深干脆把鸦巢的根据地给拔掉了。获得“乌鸦嘴”称号最鼎鼎有名的人是球王贝利,世界杯比赛期间,球王看好哪支球队,哪支球队就提前出局。所有那些雄心勃勃的球队都忌讳被球王赞扬。 然而乌鸦偏偏不识趣,对人类仿佛有宿世情缘。乌鸦喜欢把巢修在离人家很近的大树上。是因为聪明爱接近人类,还是固执地要为人类担任瞭望哨报警员的角色? 老家那一带,乌鸦最爱偷吃的是腊肉。晒在场院里的腊肉要用网网好,一不小心就被乌鸦啄得稀烂。乌鸦偶然还会啄小鸡。但多数时候,乌鸦和人都相安无事。我家门前,靠河边隔得很近的两棵大树,——一棵枫杨树一棵椿树上,都有一个鸦巢,从来没有人想过撩竹篙子把它挑掉。 我童年时听祖父说起过,他带领一家人在小村拓荒定居下来的头一年,并没有看见过一只乌鸦。后来又来了几户人家,有点村落的气氛了,乌鸦也跟着来了。算起来,乌鸦到小村来也有了半个世纪,算得上日夕厮混的老村坊。怎么后来它们招呼也没有一个就走了?难道是对村里人积怨已久?这对老家那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到底是吉是凶呢? 一个山村子若是长年听不见几声老鸹的聒噪,那简直不是兴旺发达的景象!乌鸦几乎从古以来就是村落的象征。远行的人当夕阳西下要寻宿处的时候,一听见乌鸦叫,必会额手称庆:前面定然有个村落! 但是老家一带的村民并没有歧视排挤过乌鸦。他们当然不懂对大自然中的草木鸟兽表现出一点绅士风度或慈悲心肠,更谈不上对自然有多敬畏,无非因了沉重的生计压得他们顾不上生活外的事。那时候山上草木芃芃,鸟兽蕃滋。河水丰沛,鱼又多又大,村里人都没闲工夫去捕捞。况且乌鸦鸣声嘶哑,毛羽也不绚丽,就更不受人白癜风好了浙江治疗白癜风疗效最好医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ujuanhuaa.com/djhhq/3037.html
- 上一篇文章: 路近景美体验大西安的城市观鸟圣地
- 下一篇文章: 苍山西坡,杜鹃满山,又是一场如约的花事